 原标题: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 青春读书会
原标题: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 青春读书会
导读:
《学习时报》1999年9月创刊,中共中央党校主办,面向全国,服务全党,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,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。 1985年6月...
《学习时报》1999年9月创刊,中共中央党校主办,面向全国,服务全党,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,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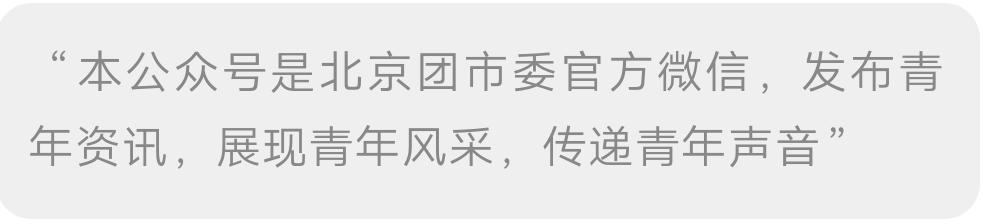
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,习同志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,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、开拓者。他领导制定了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,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,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,大力度推进生态环保工作,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,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。厦门3年,习同志一心为民、严于律己,勤于工作、勤于调研,敢于担当、敢于创新,展现出对大势的科学把握和远见卓识。他深有感触地说:“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。”
采访对象:王金水,1934年5月生,福建安溪人。1979年至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、市委、市政府党组书记,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,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。1999年10月退休。

习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,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呢?今天我们来接着听听王金水的讲述。
王金水说,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,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,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。上世纪80年代,厦门搞特区建设,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,到了夏天臭烘烘的,苍蝇蚊子满天飞,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。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,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,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。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,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:“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,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,您要经常到厦门啊!”他回答我:“好啊,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,我就来。”这是一句很重的话,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。
后来,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,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。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,但要花钱——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。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,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。这1000万要不要拿、怎么拿,市政府感到很棘手,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。当时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,分管财政,他很支持这项工作,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,这笔钱就从同志手上批下来了。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,人大代表提案,中央领导检查督促,连续3年,总共投了3000万,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。这个事情是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,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,就是: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。
在保护环境方面,我听说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,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。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,福建就有两个: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,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。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,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,就是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,才保护下来的。
王金水说,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,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跟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。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,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。他当时说:“有一个事,要跟组织报告,今天到厦门了,明天我们要结婚。”我说,这是个好事啊。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。第二天,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。他说,不举办什么仪式了,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。
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,住在市委宿舍,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。饭后,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,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。他很痛快地说:“来吧!”我们去了四个人,我一个,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、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。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,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。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,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,还有两个碗,这才凑齐了六个。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,花了5块钱。我们还开玩笑,说我们一共四个人,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?说,不好意思,没给你们准备礼物。吕拱南说,你有礼物,你唱歌就是礼物。她说:“行,我就送你们一首歌。”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。后来有一种误传,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,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。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,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。
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,同志给我讲,周日要带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。第二天,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,住了一晚上,住宿费、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。在30年前,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。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: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,受益终身;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,受害终身。
王金水与习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,正是特区建设初期,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。王金水说,那几年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,很少有周六周日,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。但我知道,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。你看他访问法国,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。我曾经问他:“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?”他告诉我,是逼出来的。他给我讲,他在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,不能带笔记本,开会时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,只能凭脑袋记。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,然后背,背熟了再烧掉。当时也没手机,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,一个字有几个号码,都是靠背。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。
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,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。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,我也喜欢,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。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,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。而省人大开会期间,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。休会的时候,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。
当时,同志住在图强路,我和他是邻居。来厦门的时候,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。有一次,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,就问:“怎么没有来打饭,让你来打?”说,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,早上就起不来了。跟我说:“一看到书就‘醉’了。”所以说,埋头工作、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、生活的全部。
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,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,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同志。同志问他:“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?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?”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,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,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。回来以后,他给我讲了这件事,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,没想到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,连最偏远、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,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,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。
同志很尊敬老同志,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,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,要么给我打电话,要么到我办公室,来听听我的意见。后来离开厦门以后,尤其到了北京,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。不是打印的,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。到了第三年,我给他打电话,说你现在日理万机,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,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,我也不再给你寄了,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。他同意了,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。但是逢年过节,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,讲很多祝福的线年他回到厦门,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,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,对我们很热情。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、朋友介绍我时,不说我的名字、职务,而是给大家介绍“这是我的老班长”。他离开厦门30年了,不仅没忘记我们,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。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。
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(第四期)学员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(民政部培训中心)培训部主任 副教授 孙钰林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